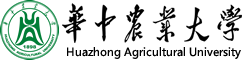西北的夏日干燥酷热,草丛里的蝈蝈声嘶力竭地振翅高鸣,仿佛发泄着对夏天的不满。黄土地的麦子簌簌地被西风吹拂着,一根根麦子之间挤来挤去,饱满的麦粒似乎就要喷泻而出。麦子成熟了,可这番景象也只能在一些落后的村落才能看见了。
老白杨在西滩村活了一辈子,与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,到了今天的光景,土地被租借为建设用地,他只得依靠每月一点不多的租金过活。
“当初不把地租出去就好了。”老白杨总喜欢坐在自家门前的小土墩上,一口又一口地吮着自己卷的旱烟。两个儿子不甘于自己囿于着一方贫穷之地,读完高中就告别父老去县城打工挣钱了。不过,最近几年也算熬出了头,在县城买了一套不大的楼房,有了子女。孙子是老白杨除了那一亩三分地最大的盼头,老白杨宁肯自己受苦受累,也要满足孙子提出的要求。以前,农忙时节,老白杨是西滩村的大红人,因为乡村留下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割麦、收麦等农活都是上了年龄的老人一家帮一家去完成。老白杨作为留在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,农忙劳动的重任自然轮到了他的肩上,帮完这家帮那家。
西滩村除了自己家,麦场就是大家最重要的聚集场所,重要会议、处理麦粒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麦场不大,由几座土坯房、麦子组成的草垛和空旷的黄土地组成。它更像是一个用来祭祀的场地,祭祀的仪式被称为“碾场”。当早上的太阳还未给大地涂抹上一层金黄的时候,男女老少就从炕上起来,就这自家做的饼和刚泡发的热气腾腾的茶,填充自己饥肠辘辘的胃囊。
把该用的农具扛在肩头,就像肩负着一家人生的希望。戴上草帽,挽起裤脚,边向着麦场大步走去,不时和路人打上一声招呼。
农村的路就是这样,走在路上的人多了,踩在地上的力度重了,不免会使轻盈的尘土飘起来,说是尘土飞扬,倒不如说成迷雾四起,扛着农具的人们走在中间,就像一幅迷幻的电影海报。老白杨自然是来的最早的,哼着小曲,在土坯房屋檐下等候已久。老白杨年轻力盛,就让他去牵引背后拉着碌碡的老黄牛,牛的背像远处的山峰一样,高低起伏,清晰可见。
一捆捆麦子被平铺在麦场的中间,围成一个圆形,也许从空中看,还以为是什么神秘怪圈呢!老白杨和老黄牛,一前一后,徐图缓行着,一粒粒藏匿于金黄色外壳中的麦粒被碌碡轻柔而又无情地挤了出来,跌落在麦子铺就的大地上。
一圈又一圈,好像暗示着一代代人出生、逝去,万物都是这个理儿。老白杨黝黑的皮肤已经有些绯红,汗珠从鬓角不断滑落,麦秆也从圆柱形变成了一张张薄纸。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,太阳高高悬挂在空中,饭点也到了。农村的午饭简单朴素,以填报肚子为优先目的,妇女们有的抱着一个油绿绿的大西瓜,有的带着一竹篮的馒头,有的两手端着菜,还有的提着茶壶。老白杨和他一样的年轻人们与老人们围成一圈,盘坐在巨大的黝黑的草垛阴影中,年轻人搛菜给老人,老人给年轻人,你来我往,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往事。饭毕,切开西瓜,殷红的瓜瓤裸露出来,一人一角地大快朵颐。顾不上靠在柔软的草垛上多休息一会,吃完饭,休息片刻,就得开始下一轮劳作了。
左手执木叉的前端,右手执后端,把支离破碎的麦秆从地上抛到空中,等待风的洗礼净化,多余的杂物被风从麦粒上剥离下来,麦粒砸在地上,麦衣就随风而去,飘到麦场外,飘到遥远的未来。若是有幸借到大型风扇,就可不必看老天爷的脸色了。
临近傍晚,晚霞弥漫在空中,催促着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该奏响结束的终章了。老白杨和几个年轻人将麦粒用扫帚汇聚在一起,装进一个个蛇皮袋子。这袋子里是人们生存的希望,是丰收的喜悦。
“爸,我带孩子来看你了。”大儿子从路口传来的声音,把老白杨从回忆中拉扯了回来。只要老白杨坐在自家门前的土墩上,他总是会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。
“爸,孩子放假了,我带他到乡下玩儿几天再回去。”,大儿子边说边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苹果给老白杨。
“好好好,爷爷给你杀只鸡吃”,老白杨起身接过苹果。
傍晚,老白杨把鸡圈里的母鸡变成了一盘美味的大盘鸡,孙子低头啃着鸡肉,老白杨的手艺显然得到了挑嘴的孙子的夸赞,大儿子和老白杨聊着最近发生的事儿,从小家到国家,大儿子一直想把老白杨接到城里住几天,享享清福,敬敬孝道。所以,大儿子言语间总是在强调城市的发达、舒适。
老白杨当然知道城市有城市的好,可他也晓得乡村有乡村的好,金窝银窝,不如自己的狗窝。
老白杨不服老,他总认为自己还有力气,就像年轻时那样,可他现在连蹲下来有时都显得吃力。
“我哪里都不去。”,老白杨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大儿子。大儿子见父亲拒绝,也不好说什么,只好作罢,也低头默默撕扯着鸡肉。
因为在县城上学的缘故,孙子很少来到乡下,对乡村田野的一切总是充满好奇。
“这是什么花?那是什么草?羊吃这个吗?”,孙子和老白杨一问一答地走在刚刚修好的水泥马路上。
老白杨是个喜欢念旧的人,逢人就讲以前的日子有多好多舒适。
“以前路边都是鲜花野草,走在路上都是香喷喷的呦!人喜欢香味,牛羊更喜欢吃。”
“水渠里都可以看见水底的石子儿,晚上睡觉不用关大门。现在世道变了,人也复杂了,心眼多了。”,老白杨声音轻柔地似乎只有他自己能听见。
有时候,老白杨喜欢扛着农具去已经被出租出去的地里去看看,站在田垄上,一站就是好久。
村里人看见了也会打趣道:“哟!去种地呐!”。
老白杨也见惯不怪,用一个微笑和一个点头就应付过去了。自从老白杨的妻子去世后,老白杨更喜欢去田地里了,总是一个人坐在哪里自言自语。快过年了,两个儿子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媳妇和孩子回乡下陪老白杨一起过年,吃饭的时候二儿子随口提到自己看到的新闻:“国家现在保护耕地,重视粮食种植了,不然大家没饭吃了。”无意之谈,却深深地烙在了老白杨的脑海里。
晚上,老白杨没睡着,翻来覆去,总感觉自己胸口有一团火在燃烧。他踩着自己的布鞋,身上披了一件外套,借着皎洁的月光,蹑手蹑脚地去放着农具的南房。月光如洗,给农具披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,气氛清冷而神秘,老白杨把自己厚实粗糙的手慢慢放在农具上。
“老伙计,老伙计!你好好地休息吧。”,老白杨一口一口呼唤着,好像农具有了性灵一般。满足了自己的念想,老白杨又回屋睡觉了,这一觉他睡得很香。不像城里过年满街挂红披彩,乡村里的年味倒显得淡了许多。一大早,除了几声狗吠和鸡鸣,人们还没有从昨夜的觥觞交错中缓过来,仍然在呼呼大睡。
待到来年入夏,老白杨不知从那里弄了一捆麦子,左肩扛着木叉,右肩提着那一捆麦子,径直往麦场走去。
“怎么想起去碾场了呢?”,同村人看见说到。
也有的人说,这糟老头子怕是疯了。
邻居给两个儿子打了电话,把老白杨的事儿告诉了他们,两个儿子很是不解,父亲这样做是为那般。两人一起商定时间,乘车匆匆赶来,都不知道父亲葫芦里买的什么药。正好开始变天,有下大雨的征兆,两人并行走到麦场,看见老白杨正在弯腰收集麦秆。嘴里念叨着:“碾场喽!碾场喽!到碾场的时候喽!”。雨点像竹筒倒豆子一样,从乌云中坠落下来,两个儿子从疑惑变为害怕。他们一人一个胳膊,企图把老白杨架回去,可老白杨胳膊一甩,就摆脱了两人的束缚。
“这样不行,必须把爸拉回去,不然这样淋雨迟早会出事儿。”大儿子转头给二儿子说。
两人又故技重施,这次无论怎样两人都紧紧架住老白杨,把他抬回了家里。老白杨的两腿像被抓住的青蛙的后腿一样蹬来蹬去。一回到家里,老白杨就像如梦初醒一般,不再反抗,只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,似乎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。但是这次事件后,老白杨就生了一场大病。两个儿子也因此请了假在家照顾老白杨,可老白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意识也越来越模糊,嘴里总在嘀咕着:“碾场!碾场!”。
到老白杨临终的那一天,大儿子抓着老白杨的手,他的手越来越冷,越来越虚弱,直到咽气的最后一刻,嘴里仍在嚅喏着“碾场!”。也有的人说,这糟老头子怕是疯了。邻居给两个儿子打了电话,把老白杨的事儿告诉了他们,两个儿子很是不解,父亲这样做是为那般。两人一起商量了个时间,乘车匆匆赶来,都不知道父亲葫芦里买的什么药。
正好开始变天,有下大雨的征兆,两人并行走到麦场,看见老白杨正在弯腰收集麦秆。嘴里念叨着:“碾场喽!碾场喽!到碾场的时候喽!”。雨点像被撕裂了一样,从乌云中坠落下来,两个儿子从疑惑变为害怕。他们一人一个胳膊,企图把老白杨架回去,可老白杨胳膊一甩,就摆脱了两人的束缚。“这样不行,必须把爸拉回去,不然这样淋雨迟早会出事儿。”大儿子转头给二儿子说。两人有故技重施,这次无论怎样两人都紧紧架住老白杨,把他抬回了家里。老白杨的腿还想被抓住的青蛙后腿蹬来蹬去。
一回到家里,老白杨就像如梦初醒一般,不在反抗,只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,似乎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。但是这次事件后,老白杨就生了一场大病。两个儿子也因此请了假在家照顾老白杨,可老白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意识也越来越模糊,嘴里总在嘀咕着:“碾场!碾场!”。
到老白杨临终的那一天,大儿子抓着老白杨的手,他的手越来越冷,越来越虚弱,直到咽气的最后一刻,嘴里仍在嚅喏着“碾场!”。